
景柱,1966年10月生,河南兰考人,中共党员,北京大学博士后,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、海马集团董事长,海马汽车创办人、海保人寿创办人。

黑脸,在京剧中属于净角之一,代表性格刚直、铁面无私、敢于直言。黑脸也是一种人生,唱黑脸的人一般都靠谱。事不如意常八九,能与人言无二三。二三之中,都是诤友,诤友就是自己的黑脸。有时候,黑脸也是一种自然规律,违背它,就会遭到惩罚,可以理解为自然界的“黑脸效应”。
生活中,我有个发小叫黑脸,比我大几岁。当时,黑脸爹游手好闲,到处瞎跑,那个时代叫“流窜犯”。黑脸一岁时,黑脸娘被黑脸爹饿跑了,因为不跑就得饿死在家里。因此,黑脸从小没娘,和他奶奶相依为命,当然上不起学,一直是文盲。
黑脸人穷志高,从小跑着活命,见识比我大得多。我小的时候,很崇拜黑脸,上学前后,有事没事都找他玩。冬天,黑脸到田野里拾坏红薯,卖给供销社做酒;春天,黑脸在田野里刨桐树根,卖给供销社育苗。所以,黑脸手里一直有“钱”。
我第一次学喝酒,就是黑脸教的。有一天,黑脸喊我晚上到他家喝酒,我一放学就跑去了。黑脸先从供销社买了一斤散装的红薯干酒,天黑后又窜到生产队的菜地里,熟练地“弄”回一把蒜苗,清炒了一大碗。接着,我们几个在他家的煤油灯下喝起酒来。我当时很激动,觉得自己喝酒了,就是一个大人了。
黑脸家南侧是刘爷家。那天晚上,刘爷看见我和黑脸学喝酒了,第二天一早就跑去告诉我娘了,接着我就挨了一顿娘揍。
过了几天,黑脸告诉我,茄子可以生吃。后来再面临娘揍时,索性不回家吃饭了,跑到生产队的菜地里,“弄”个生茄子充饥。
突然有一天,黑脸爹回来了,给黑脸带回一个后娘,应该是云南四川一带的,说起话听不太懂。黑脸后娘来到后,住进他家仅有的两间土屋里。黑脸就在院子中挖了个地窖,带着奶奶,冰天雪地时住进了地窖。即便如此,黑脸仍然起早贪黑,吃苦耐劳,劳动生产,孝敬年迈的奶奶,养活游手好闲的爹娘。
过了没多久,黑脸揣着一碗红薯面糊糊找到我,让我尝一口,结果我吃一嘴沙子。很明显,后娘在他饭里“下毒”了。黑脸从此不敢回家吃饭,跑出去流浪了,从此杳无音信。
一二年后,黑脸后娘,又被黑脸爹饿跑了,跟着同街上一个能让她吃饱饭的老光棍跑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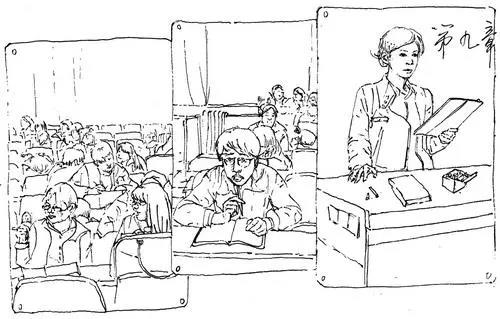
其实,无论是小人生还是大社会,都是需要黑脸的。
我读高中时期,有个同学叫张大志。同学之间闹矛盾时,打抱不平、唱黑脸的都是张大志。那个时候他爱写打油诗,有一天,语文老师宋二水念了一首给我们听:“大志有大志,大志立大志。大志存大志,大志成大志。”
大志学习很努力,就是考不出好成绩。晚自习过后,同学们都回宿舍睡着了,大志继续在教室挑灯夜战。三更半夜时,大志黑灯瞎火地摸回宿舍,经常踢到别人的洗脸盆,嘴里骂骂咧咧,鸡毛狗不顺的,惊醒了一屋子的同学。
高二上学期时,家里供应不起他了,大志辍学了,从此也杳无音信。
改革开放初期,一个叫张良修的人,作为致富能手,被县里连续隆重表彰了好几年。说他从小失学,全国各地跑着打拼,卖过老鼠药,刻过印章,还倒卖过帽子,最后在北京做建筑涂料发家了。张良修致富不忘家乡,带领村民到北京发展,在京郊建了一个“兰考村”。有一年,张良修回老家过年,说是从北京开回了五十几辆捷达。
我一直不认识张良修。就感觉兰考先出一个焦裕禄,后出一个张良修,因此对他很崇拜。2000 年,在县领导的撮合下,我和张良修在北京见面了。闹了半天,张良修原来是黑脸同学张大志。
我和大志重新接上头后,双方互当黑脸、互为诤友。曾为一件事,我俩争得厉害,一二年相互不搭理,但感情却越来越深了。后来我一直在想:学历不等于能力,文凭不等于文化,职称不等于称职;出门看学历,长期看能力。我从小学习好,读了半辈子书,事功也没做多大;大志从小学习不好,基本没读书,事功做得也不小。双方门不当户不对的,为啥能成为诤友呢?就是因为相互容忍一个生活中的黑脸吧!
北京奥运会之后,一些国人迷糊了,误认为中国“发达”了。计划经济那一套已经丢了,市场经济这一套又看不上了,于是开始“任性”了,有些“一刀切”管理,甚至违背了常识,结果市场越来越不买账了。我想,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,也是一种“黑脸效应”吧!
“千人之诺诺,不如一士之谔谔”。一个社会,黑脸少了,白脸多了,就是一种病态。
——行者2020年4月25日于樱花楼